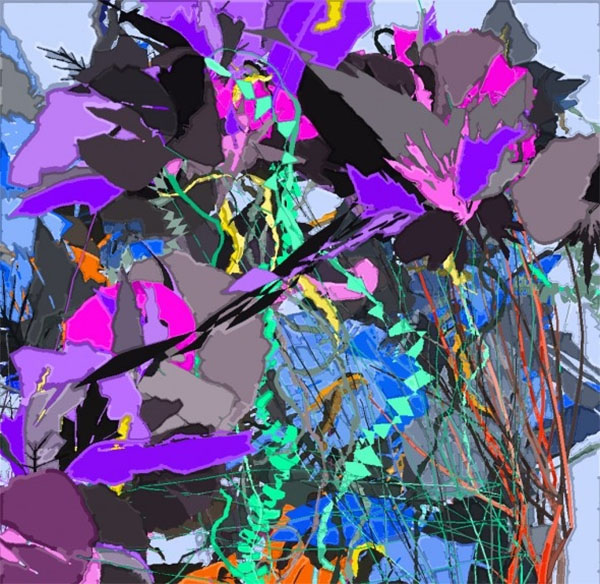2013年7月,一名崭露头角的艺术家在巴黎Galerie Oberkampf举办了展览会。展览会持续了一周时间,民众前来观看,新闻媒体广泛报道,一些作品花了多年时间创作,还有一些直接画在画廊上。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场典型的艺术展。唯一不同的是这名艺术家不是真人,而是一个名叫“The Painting Fool”的电脑程序。
光是这样还不够新奇。很久以前就已经出现了AI辅助创作的艺术品。自1973年开始,Harold Cohen(画家,San Diego加州大学教授,他还曾代表英国参加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就一直与电脑程序“AARON”携手创作。AARON已经自动绘画几十年了。20世纪80年代末,Cohen曾经开玩笑说他是唯一一个后死仍然可以举办新作品展览会的艺术家。
关于机器艺术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首先,它的潜力如何;其次,姑且不考虑作品的质量,它真的算得上是“创作”并且“富有想像力”吗?问题深刻而迷人,它引领我们进入到人类艺术制作的神秘谜团之中。
The Painting Fool是Simon Colton的“作品”。Colton是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计算机创作学教授,他认为要让程序创作,先要跨过一些与图灵测试不同的测试。图灵测试要求机器按人类的方式进行可以信服的交谈,Colton却认为AI艺术家要让自己的行为变得“富有技巧”、“可以欣赏”、“富有想像力”才行。
对情绪作出反应
到目前为止,Painting Fool已经在这三个方面取得了进步。所谓的“欣赏性”,按Colton的意思就是对情绪作出反应。Painting Fool的早期作品由图片拼成。程序先要扫描英国《卫报》一篇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文章,从中提取关键字,比如“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和“英国人”,然后寻找与之相关的图片。找到之后程序用图片制作合成图,以反映报纸文章的“内容和情绪”。
软件可以复制不同的绘画和图形媒介,从中挑选合适的,然后评估结果。它曾经这样评价一幅画:“真是悲惨的失败。”怀疑者认为这些描述只不过是哗众取宠的数字口技,而软件官网却说诗化的写作正是当前的一个项目;只有这样Painting Fool才能成为作家和画家。
在巴黎展会上,想画肖像画的参观者坐在一台电脑前——不是人类艺术家,电脑会在屏幕上“绘画”。The Painting Fool根据不同的情绪为访客绘画,它会提取情绪关键字(从《卫报》的10篇文章中提取)然后作出反应。如果感受的情绪太过负面,软件会意志消沉并拒绝绘画,相当于虚拟的艺术气质。
2015年6月时,谷歌Brain AI研发团队公布一张图片,它至少从一个方面折射了人类的想像力:认为一件东西是另一件东西的能力。研究人员训练软件识别物件(根据视觉线索识别),然后输入天空照片和任意形状的素材,程序得到的建议是将迪士尼、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的想像力进行结合,它开始生成数字图片,包括“猪-蜗牛”“骆驼-鸟”“狗-鱼”的混合体。
在莎士比亚的著作《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中,安东尼曾说过这样的话:“有时我们看到云彩像龙一样,看到蒸气像熊或者狮子。”这是一种心理现象,程序此时的行为相当于这种心理现象的数字版本。
达芬奇建议我们可以通过凝视墙上的污点或者随意性标记来刺激创造力。艺术家努力从中“发明一些场景”,他们可以“看到”战场上晕眩的战士,或者一片景观,里面有山、河、石头、树、大平原、山谷和山。
石洞壁画的灵感可能由此而来。绘画或者雕刻石头经常会利用自然特性——例如墙上的鹅卵石看起来像眼睛。克鲁马努(旧石器时代晚期生活在欧洲的高加索人种)艺术家最开始可能利用随意性特征来识别狮子或野牛,然后通过绘画或者雕刻让动物的肖像变得清晰起来。所有的具像图片(不只包括图画,还有照片)都依靠这种能力将一件东西(平面上的图状)看成另一种东西:3D世界中的东西。
谷歌Inceptionism
谷歌开发的AI系统擅长于做这样的事。图片是由人工神经网络创作的,也就是用软件模拟大脑神经元处理信息的方式。软件先要接受训练,通过分析数百万个实例进行训练,然后才能识别图片中的物体:一个哑铃、一条狗或者一条龙。谷歌研究者发现,按照达芬奇的建议,他们可以将系统变成“艺术家”。先向神经网络输入一张图片,上面满是斑点,然后命令网络进行调整,软件之前已经识别了一些物体(训练出来的),它要从班点中寻找任何与物体相似的地方。此时软件做的事和安东尼从云彩中看到动物是一样的。谷歌团队将最终的艺术风格叫作“Inceptionism”,因为神经网络架构的研究项目代号为“Inception”。2010年时曾经有一部电影也叫《Inception(盗梦空间)》,它讲述了一个男人深入他人大脑梦境的故事。
站在艺术的角度来看,你可能会将Inceptionism当成超现实主义的一个变种。雷尼· 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和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创作了许多超现实主义作品。
Inceptionism到底怎么样呢?一些画作很惊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欣赏,比如线条的风格模仿梵高。至于Inceptionist作品还是太普通、太像照片了,太像达利或者马克斯·恩斯特的作品。不论是Painting Fool还是其它相似的程序,水平连高中生都不如,连业余艺术俱乐部的标准都没达到。计算机艺术的潜力在哪里?人工智能可以为视觉艺术增添风采吗?
Simon Colton已经意识到批评的存在,人们认为Painting Fool的作品只属于它自己。Simon Colton说,如果人类画家画了一幅画,我们不会将赞美对准画家的老师。那么赞美应该给谁呢?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回到过去
文艺复兴时期,工作室的画如果赢得赞扬,荣誉归老师所有,学生没有份,尽管他们完成了相当一部分的作品。但是在Verrocchio创作的《Baptism of Christ》(约1475年)中,我们看到了工作室成员达芬奇的造诣,因为他画的那一部分(天使和一些风景)与老师的完全不同。艺术历史学家将这幅画视为联合创作的结果。
在17世纪的Antwerp(安特卫普),鲁本斯有一个小工厂,里面招纳了一些接受过高标准训练的助手,鲁本斯绘制大尺寸作品时,这些助手或多或少参与了大多数作品的绘制。一般程序是这样的:老师先绘制小幅草稿,然后在老师的监督下,画作慢慢填充到天花板或者祭坛上。一些学者认为,有时工作室的作品虽然标的是“鲁本斯”的大名,但实际上连画的原始模型都有可能不是他提供的。
历史为AARON提供了有趣的例证。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不断进化的程序绘制了许多画作,它们到底是Harold Cohen的作品还是AARON自己创作的?或者是联合创作的?这可是一个微妙的问题。AARON从没有跳出20世纪60年代Harold Cohen的基本创作风格,他当年曾是色彩领域抽象概念的代表人物。从这个角度来看AARON是他的学生。
Cohen之所以会对AI感兴趣,因为他觉得“艺术创作不一定需要持续作出决定……我们应该可以设计出一套规则,不需要深思就可以按规则绘画。”
办法就是总结某一类艺术家的特征。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创作的抽象画就是一个好例子。这些作品是根据一套规则创作的:只允许使用直线,只能以直角相连,只能用红蓝黄描绘(加上黑和白)。
在艺术史上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这是一个很罕见的实验:艺术评论家Tom Lubbock根据规则绘制一些蒙德里安风格的画。他创作了几张抽象画,看起来很像蒙德里安的作品,只是不太好。实验得出的结论就是蒙德里安为画作增加了一些独特的气质,我们无法按规则模仿出来,可能是视觉上微妙的平衡,也可能是色彩的搭配。
艺术批评家像Lubbock一样进行实用性研究是相当罕见的,有许多人(并非艺术评论家)在做同样的事:我们管这些人叫伪造者、抄袭者或者学徒。艺术品中模仿之作并不少见:人们根据蒙德里安、莫奈或其它发起人的风格绘制画作。艺术历史学家终其一生给艺术家分类,比如“波提切利圆”“ 卡拉瓦乔的追随者”等等类别。很显然机器可以在某个层面上进行创作:它们可以绘制派生艺术品(99.9%的人类艺术家都是这样做的)。那么机器有能力打破这种限制吗?
让AI学会配色
关于这点Cohen思考了很多。2010年Cohen曾发表过一篇演讲,当时他从相反的方向来看待问题。AARON的创造力难道不明显吗?Cohen说:“我不需要继续输入信息,它就可以绘制无数的图片,比我更擅长使用色彩,当我躺在床上时它就在作画。”“有人问,这是他自己创作的吗?”“没错,程序是我写的,我制定了规则,程序只是简单的遵守规则,这样说完全正确。程序本身就是规则。”
然后,AARON就像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代的工作室一样自己作画。根据Cohen的指引,AARON可以确定主题,相当于自动模式的鲁本斯工作室。在最开始的几年,AARON只是绘制轮廓,Cohen会挑选出一些作品,有时还亲手配色。20世纪80年代时,Cohen开始教AARON使用色彩。最终,Cohen制定了一套规则让AARON配色,效果不尽人意。他的第一套解决方案由一长串指令组成,指令介绍了人类艺术家在特定情境中是怎么做的,可惜的是指令并非总是管用。
最终,他开发了一套简单的算法教AARON使用色彩。在不同的色彩搭配上人的想像力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反馈系统很棒。人类艺术家注视着画作,当绘制工作步步深入时,他可以决定画中的向日葵到底用什么样的黄色阴影更好。AARON没有视觉系统,Cohen设计了一套算法,随便给一张图片,它就可以在色调、饱和度等方面作出平衡。
那么机器能够像Rembrandt或者毕加索一样富有创造力吗?要做到这点,Cohen认为机器必须先要学会自我感知。未来可能会,也可能不会。Cohen说:“如果没有形成自我感知,机器的创造力将永远不能与人类相提并论。”在整个过程中艺术家需要让社会、情绪、历史、心理、生理等因素相互作用,光是分析如此复杂的过程就比登天还难,更别说复制了。艺术家绘制了一张画,在人类的眼睛看来之所以意义深远,原因正在于此。
Cohen还说,某一天随着进化的深入,机器也许会变得同样敏感,即使这一天没有到来也并不意味着机器就一定与创作无缘。从Cohen的个人经历来看,AI为艺术家提供的帮助已经超出了助手或学徒的范畴:它已经成了新的创作合作者。